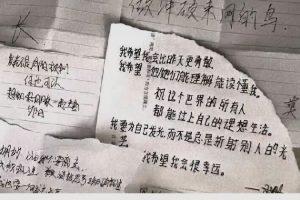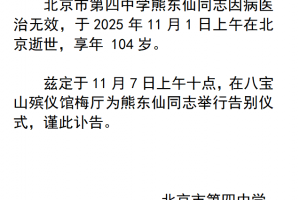北京四中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有着良好的声誉,是一所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一流名校。江在任时于1995年到四中考察时说了16个字,“四中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到此、三生有幸”,这16个字的后三组12个字,用在哪里都是最高的荣耀,无论是清华北大,还是香港澳门。这是历来到过四中的大人物中,地位最高的人给出的最高的评价。
那么,北京四中究竟“好”在哪里呢,我们从三个方面仔细分析一下。
一、校园
北京四中东西北三面临街,东面的街道我们上学时叫“后库”,现在统一称之为西什库大街,我们上学时的正门在东边;西面是西黄城根北街,现在正门开在了西面,东面的门反而成了后门了;学校的北面是地安门西大街,这一点没变,只是拓宽了;学校的南面与人大常委办公楼为邻,几十年没变。这四面都确定了,可以得知四中的校园大致是一个正方形,每边大约200多米。
2020年是鼠年,在120年前的那个鼠年,也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大清朝战败,赔款不说,还得给联军战死的人修墓地。那个时候不兴搞强拆,朝廷只能在自己的身上下手。“后库”顾名思义就是“西什库”的后面、也是储存各种杂品的仓库,朝廷就把这块地腾出来给八国联军做了墓地,其中法国人死的较多,统一埋在了这块地的东北角。
“庚子赔款”之后,美国带头退还了部分赔款用来兴办中国教育,清华就是用这笔钱创办的。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1906年顺天府在后库筹建“顺天中学堂”,1907年正式招生开学,1912年9月更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在筹建的过程中,西方列强也是支持清政府兴办教育的举措,墓地也就迁的迁、平的平,只有东北角的法国人墓地有专人看守,态度强硬,没有拆成。所以四中这个大方块缺了东北一角,总共占地面积大约45000平方米,约合67亩地。1949年以后,新建的政权不认这个邪,就在东北角的法国人墓地上,建起了“中直招待所”,用来招待来京的各省大员,改开后升级变成了“金台饭店”。1965年我们在校时搞战备挖防空洞,在操场的西北角还挖出了不少的水银,也可以佐证是当时为给八国联军建墓地而匆忙搬家时遗撒所致。
四中的校园在北京不敢说最大,但也是名列前茅,最可贵的是有一个市区内的学校绝无仅有的400米跑道和标准足球场,这是四中的骄傲,每逢教育界有大型活动,四中操场必是首选。四中在1950年代修了一座教学楼,无暖气无厕所,只能装32个班,离当时中小学六个年级各六个班的共36班的标配还差4个班,我们刚进校时是在南墙边上的平房上课,初二才进的教学楼。因此上说,当时四中的校舍不算是先进的。四中的教学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校图书馆藏书十余万册,在当时可以和一些大学相比,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上生物课用的显微镜,我们上课是一桌一台,也就是两人一台,我们的小学同学上了其他学校,就是老师讲台上有一台,同学们排队上去看。1965年日本乒乓球运动员松崎君代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很喜欢她,其间她来到四中参观,为了这次活动,上级一次就拨给四中十台国际比赛用的标准乒乓球台,这在当时就是发了一笔小财。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四中进行了一次毁灭性的“改造”,所有的建筑除了老校长室是原拆原建保留原来的风貌外,所有的建筑全部拆掉重建,全部“平改楼”,最为有名的大操场也扭了个90度,因为不符合国际标准,国际标准的体育场全部是南北向的。 原来在校园东侧的校门,那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建筑,设计者是谁已不可考,但是谁都看得出来,四中的校门和清华大学的校门很是相似,人们都说进了四中就等于进了清华!现在看来,这两个建筑是有惊人的风格一致之处,也不知是谁模仿了谁,从建校时间来看是四中在先,但也不排除是后改的校门。现在从大街上已经看不到四中的老校门了,在2001年西什库大街的改造扩宽工程中,这个老校门被拆掉了,为了留下这个四中人心中魂牵梦绕的地方,学校在四中操场的东南角重修了这个标志性建筑,现在人称“克隆门”。
小结一下:四中的校园够大,建筑有特点,但是校舍不新,很多都是民国的老房子。四中的教学条件是一流的,领先于当时其他中学,这得益于它的名声。
二、教师
四中之所以闻名于世,不在于它的校舍多么大、教学条件多么好,而是四中有一批非常厉害的老教师,这批老教师在当时可以称为一时之选,这里边不乏有大师级的,他们带领着年富力强的骨干教师,还有刚刚留校的高中生教员 ,他们一代代传承着,传承着四中的光荣,传承着四中的骄傲,他们有以下几个特点。
1、有尊严
尊严是什么,这说起来很抽象,看不见摸不着,似乎可有可无,其实尊严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文化传承的命脉。尊严是一种力量,一种令人敬佩、令人信服的吸引力,平时人们管这叫“派儿”,“有派儿”是人们对值得尊重的人的一种非常高的评价。四中的教师们尤其是中年以上的教师,和蔼的面庞上流露出一种威严,严肃的脸上还可以看出内心的慈祥。正式这种尊严构成了四中的校风,全校之内,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表敬意,从教师之间传到了师生之间、传到了同学之间,从在校期间延续到出了校门之后,又延续到了后代身上。
从1949年以后,社会上的称谓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教师不再被尊称为“先生”,通通的称为老师,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可是四中校内对教师的尊称还是先生,主要是对老教师,一直叫到了“文革”,连我们这些64年进校的小孩子也跟着高中的学兄们一起叫。可见,四中这些老先生们身上的尊严,也就是人格魅力不是因时代不同就能消失了的,这是他们对自己教师身份的骄傲、对自己教书生涯的一种自豪、对学生们的一种热爱,这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不是装的,装也是装不出来的,尊严对于这些老先生们来说,是比生命还更重要的品行。文革中曾一度批判“师道尊严”,其实这种尊严不是一批就能批没了的,这是多年养成后与生俱存的。经过这么多年的批判,尊严在当下的教育界几乎是没有了,都发生了校长搞老师、老师搞学生的丑闻了,何来尊严!
在四中的师生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文革”前某天的一个下午,某教师正在教员室批改作业,这时进来了一位解放军,问明他就是所找之人后,走到跟前向他说,我是某首长的秘书,他的儿子某某某是您的学生,首长今天有空,派我带着车来接您,想了解一下某某某在学校的表现。这位教师沉思了一会说,您也看到了,我正在批改全班的作业,我是全班40多人的老师,不是一个人的老师,您把地址留下,等有空了我骑车去拜访首长。这个故事之所以传开,并都为某先生叫好,皆因四中校内的风气很正、价值观相同。这位首长当时官拜全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这种机会放在当时的别的学校别的人身上,足够吹一阵子了!(现在文中的当事人均已故去,所以用某代之。)
尊严是四中校风中的精髓,靠着教师一代代传承,也可以说是四中的灵魂。(有一段话放在第四部分再说)
2、有修养
如果说尊严是形而上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道不明,有者或需要者视之重于生命,无之或弃之者则看为一钱不值;那么修养就是形而下的具体表现了。修养看得见摸得着,说得清道得明,有者傲视同侪,无者装之趋之。这种修养现在很多人叫做“范儿”,言谈举止之中令人敬仰并值得模仿。
四中的老师有修养,表现在外在和内心两个方面。外在的修养在当下有许多的表现,如开车有车品,吃饭有吃相,看演出有看演出的规矩等等,但在那时候学生观察老师,主要就是看外表,也就是看服装。四中老师的收入不低,完全可以穿戴得很好,但是四中老师的服装都只是追求得体,不管穿什么都显得一看就是老师,有的女老师穿一件大襟上衣,也显得和宋庆龄一样的气质。现在我们都老了,回想起来总的说就是两个特点,一个是质地好样子老,样子太新容易让人有奇装异服的感觉,质地好说明社会地位和收入,样子老说明遵规守矩;第二就是合身。每个人的高矮胖瘦都不一样,衣服都应该因人而异,再好的衣服不合身也是白费钱财,四中老师的服装都非常合体。人们每天都照镜子,有的为了美有的为了雅,四中的老师也不是不讲究穿衣,在我们上学的那个年代,这就是在社会大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为讲究的穿衣方法了,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修养。如果你现在在机关里、在学校、在医院,如此穿衣还是会获得赞许。
修养的内在表现就太多了,四中老师人人都用自己的言行诠释着,使我们几十年了都如沐春风恍如昨日。我们上初二时的语文老师廖先生,有一天来上课,穿着一件呢子大衣,我们起立敬礼后,他还礼时鞠躬鞫得格外的深,然后说,我今天感冒了,大衣就不脱了,请同学们原谅。我们说过,当时的四中教学楼没有暖气,教室里有一个煤球炉子,时好时不好的,教室里很冷,有的同学也不脱大衣,我们根本没想到廖先生为这件事还很郑重的说明一下,表达了对同学们的尊重。廖先生上课时总是把手表摘下来平放在讲台桌上,以便掌握时间,基本上是讲完下课铃响,从不拖堂,这一是尊重同学,二是尊重下一节课的老师。笔者不才,也在中学教了十年书,我每一节课也都学着廖先生,摘表放在讲台桌上,也从不拖堂。就凭这一点,我在《少小离家老大回》一文中讲到过,为了调动我去试讲,话音落铃声响,该校长当时表态您回去办手续吧,为这也得感谢廖先生!还有一位朱先生没有教过我们,听高中的说,他一上课看到有谁因天热挽着裤腿,就走到谁的跟前说,放下来放下来,成何体统。我们四中是男校,又没有女生,穿制服裤衩行,挽裤腿不行?对了,这就是体统!上体育课后,夏天都会把扣子解开,去水龙头处用凉水冲冲,这是你碰到那个老师都会让你赶快记好扣子回去上下一节课,在校内绝对不允许敞着怀不系扣子。在校内夏天可以穿短袖衬衫,但是不能穿圆领衫,因为没有领子。修养不是虚的,它时时刻刻约束着你,在四中几年,这样的事经历的太多了。 3、有学问
说四中的老师有尊严有修养,有了这两样的老师就必定有学问,这里边有因果关系。四中校内现在有一处景观叫二老雕像,是为了纪念刘景坤和张子鄂两位老先生的,这两位老教师教书育人一辈子,都被评为特级教师,誉满杏坛。尤其是教物理的张先生,不但教好高中的课程,还能够与大学的物理课程无缝衔接,使四中的学生上了大学没有一时的不适。每每高考过后,高三的学生冲出考场高呼张子鄂万岁。刘先生是化学老师,其实四中还有一位鼎鼎大名的马老先生教数学,人称“马大代数”,这三位正好是数理化三门主课的把关人,只不过马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山东大学给挖走了,据说当时的市长彭真为此还发了很大的脾气。
这里还要说说我们的廖先生,有一年他教高三,考后教育局带着几个阅卷老师找到他,说有一个考生是他的学生,高考作文是满卷的锦绣,按水平绝对是满分,可也有人怀疑是秦牧(秦牧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文革前因其散文集《艺海拾贝》而享誉全国)未发表的文章流了出来,因为风格太像了,故而来访。廖先生看了这篇作文肯定地说,这就是他真实的水平,他完全有这个能力,他也喜欢秦牧的文章风格,又把这个学生平时的作文拿出来比照,大家都心服口服,据说这是1949年以来的第二个满分。四中的教师们,门门有带头人,科科不缺领先者,就连体育组都是人才济济,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加上田径游泳,都有高等级教师,体育组教师平均教师级别是3级,3级是当时大学讲师的水平,这在现在也是少见的,其中韩茂富老师是特级吴济民老师是1级,这两位先生都一生从事篮球的教育及裁判工作,在全市乃至全国篮球界都是有影响的人物,韩先生是国家级裁判(当时我国不在国际奥委会内所以没有国际级),吴先生是一级裁判,据说是有一次和苏联的比赛,他吹主裁临结束时延长了3秒钟,使中国队反败为胜,人家苏联提出抗议,给降了一级。有了这两位先生的指导和打的底子,四中校队一直是北京市中学联赛的夺冠或保冠球队,直到现在。前几年韩先生的雕像也立在了操场南端,守望着他一生热爱的篮球事业和市里唯一的大操场。
4、有方法
有学问没有方法也不行,没有方法是有水倒不出来,当不了老师,据说陈景润也有一段在四中的经历,就是不适合当老师才去搞研究。这个方法说来就是启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从内心想跟着你去探讨去研究,这往往决定着学生一生的走向。我们的老师们在这方面也都是各有高招。
四中每年招生6个班,大约270个学生,这都是全市近千所小学中挑出来的尖子,除了实验二小每年考上的多一些,全市一个学校平均不到一个。作为教师能够得全市的英才而教育之,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因此每个老师也都使出浑身的本事,使用各种方法来吸引同学们,想在这些尖子中再挑选些尖子,传授自己的看家本领,这与现在的老师收钱补课真是有云泥之别!
当时四中办有各科的讲座,给那些在课堂上“吃不饱”的同学开小灶。1965年我参加过一次由历史教员组组长徐健竹先生开讲的“关于李秀成自述”,那是面对高中同学的,我当时初二由于比较喜欢历史课,就厚着脸皮也去参加了,好在大阶梯教室后边还有座。李秀成在被清军俘虏后,临被杀前写了几万字的《李秀成自述》。关于这个自述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罗尔纲先生为代表,认为李秀成不是真投降,是伪降,是想借写自述之机把太平天国的一些历史留下来;另一种意见以戚本禹为主,他写过一篇《评李秀成自述》,认定李秀成就是投降,就是叛徒,并抬出了毛泽东为此批的16个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再加上当时的阶级斗争大环境(实际上已经是文革的先声),戚说一时占据上风。罗尔纲先生研究清晚期历史和太平天国史几十年,是公认的大学问家。徐健竹先生用比较客观的史实和资料介绍了双方的观点,并未做出自己的判断。其实我当时尽管是个孩子,也听出了徐先生还是倾向于罗大师的。几十年过去了,那场讲座我至今没忘,并且吸引了我一辈子喜欢历史、喜欢近代史。
在1965年元旦后的一天上语文课,我们的廖先生上课后没有马上开讲课文,而是先问了一个问题:刚刚发表的元旦社论中引用了一位唐朝诗人的两句诗,哪位同学知道?同学们互相看着,没有人说知道。廖老师又在黑板上写下了“沉舟侧畔千帆过”7个字,又问,谁能接出下一句,还是没有人知道。廖老师又写了“病树前头万木春”7个字,接着说,同样的问题我在一班(我们是二班)也问了,一班有一位同学答上来了。你们虽然还小,也要养成关心时事政治的习惯。又大致讲了讲这两句诗的作者刘禹锡的的情况。也可能是这件事情刺激了我,我从此非常喜欢这位“诗豪”的作品,他的许多诗句我至今能够背诵。
我们初一的体育老师是迟文德先生,有一次体育课下大雨,就改在教室里上,迟先生是专攻足球专业,就讲起了足球。介绍了一些常识和规则后,讲到了角球,角球有各种战术,也有时能把球直接转进球门,我们当时都听傻了,那时没有电视机,也几乎没有现场看球的机会,这怎么可能呢?球还能拐弯?迟先生讲起足球场大约是90米长60米宽,从角球点到球门中心往后大约是30米多一点,要想让球旋转进球门,就得有多么大的角度、旋出多大的弧度等等,连说带写地划了一大黑板,这时如果有人走进教室,一定是认为在上数学三角课。这堂体育课,以前没有过,那以后再也没有过。
四中的老师们,不,应该说是四中的恩师们,给我们打好了一生治学做人的底子,让我们得益当初受教一生!
小结一下:四中老师的人品修为与学问并重,提升自己、惠及学生。四中老师眼里没有权势,校长和教师只是两种工作、各不干扰,同侪之间也不傾轧,比的拼的唯有学问,颇有北大之风。文革期间我在学校,那时大字报随意写、互揭老底,我不记得有什么出边的东西。
厉害了,我的老师们!
陈国恩(67届初中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