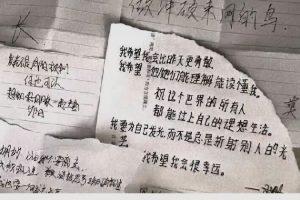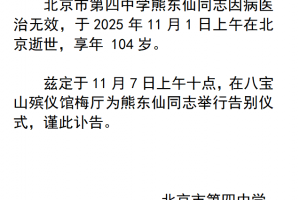一
上舟走了。他走得那么平静,又那样突然。让我完全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虽然我知道他患的是凶险的肺癌,而且已转移到肝部。可是我6月5日第三次去看望他时,他的精神明显好于我第一次去看他时的状况,而第二次去医院都没能见面,所以我怀着一份虔诚的愿望猜测,是否他的病情已经有了转机?他的小妹还告诉我,准备第二天就转到我国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院士所在的二军大长海医院。我通过电话把这个情况告知了几位我和上舟共同的好友,我们都真诚地抱有希望,希望能出现奇迹。至少能使他的生存状态有所改善,减少一些疾病带来的痛苦;至少能使他与亲人、朋友和同学们再多一点相处的时光。可是噩耗却忽然传来,让我们真诚的希望破灭了,我的心情真是难以名状的悲痛。
一些同学建议我写一篇文章纪念江上舟,作为他中学和大学时期的老同学和好朋友,这也是我心里特别想为他做的事。然而正如鲁迅先生所言:“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现在刚刚失去挚友,一些往事都还来不及静下心来细细回想。可是我也深知,既然许多老同学们都希望能看到纪念江上舟的文章,我应当责无旁贷地尽快写出来,以表达我们对他最真挚的哀思和对他永久的怀念。
关于江上舟,各种媒体上有许多文章报道。在海南工作期间,他曾任三亚副市长和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局长;在上海工作期间,曾任市经委常务副主任和市政府副秘书长;患肺癌后,还先后担任过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重大专项组组长、中芯国际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董事长和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若论他一生的功绩,在海南洋浦开发区的建设上,他是敢于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和创新的“闯海人”;在集成电路芯片产业的大规模快速发展,和我国大飞机等高科技项目的启动组织上,他都是居功至伟的功臣。在告别仪式上的大幅挽联“散英魂寄千万雄鹰翱翔神州,尽智魄载十亿慧芯呼唤华夏”,就是对他在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方面所做贡献的高度概括。这些功绩都无需我去细说。我只想从一个老同学和好朋友的角度,说说我所认识的江上舟 —— 一个不带官员身份和功名光环的普通的同学和朋友。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我心目中的江上舟,那就是“真诚”。他是一个对同学和朋友,以及对他为之奋斗的事业,都无比真诚的人。
二
记得在1963年春高一下学期时,我们北京四中高一(5)班来了一位插班生,他就是从福州一中转学来的江上舟。他身材中上,体型偏瘦,眼神总是显得又好奇又天真,喜欢问问题,说话是带着点儿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衣着非常朴素,这就是我最初的印象。上舟去世后,我曾问过几位老同学当年对他的印象,看法都差不多:聪明、单纯、清纯少年、没有被“污染”过。他因为转学耽误了好几个月的功课,而我当时担任班级学习委员,所以安排我俩同桌,我负责帮助他补上落下的功课,这样我们就很快熟识起来。
有一次课间,我说他的名字起得很不错,他随手在纸上把他的名字画成一幅画,那是一只在江上挂着风帆的船。我看了大加赞赏,就把这幅画拿给其他同学看。有同学脱口而出:“船儿!”(注:要按北京的儿化音读作一个音节)从此“船儿”就变成了江上舟的外号。那时在班级里如果你有一个叫得响的外号,说明大家对你的认可,人缘儿不错。外号往往还有延续性,像我的外号“大拿”,就从小学一直叫到大学,而江上舟的外号后来也被我从中学带到了大学。上舟去世后,我看到他大学同班同学画的一幅名字画,与我记忆的不同,至少我根据记忆画出的应该是1.0版吧。我心里更喜欢这个1.0版,因为它象征着江上舟的一生,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不达目标、决不停息。
为了方便给上舟补课,下午放学后我有时到他家去。他家住西单头发胡同,而我家在月坛南街,也还算顺路,这样很快对他们家的情况也有了了解。他父亲江一真是福建的老革命,曾任福建省长,因在“大跃进”中坚持实事求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错定为“江魏反党集团”,下放三明钢铁厂任厂长,1962年底平反后调北京任农业部副部长。我还认识了上舟的哥哥上虹和弟弟上南,他们也在四中学习。后来上舟的大儿子在上海结婚时,亲属们从各地来祝贺,我才发现上舟居然还有个小妹妹,感觉很诧异,因为过去完全没有印象,小妹笑着“抱怨”说:“你们那会儿到我家都只关心大事情,哪能注意我一个小丫头啊!”上舟的小妹说得不错,那时我们都立志为国效力做大事,平时谈论的也都是国内外的新闻和大事,从不讲究吃喝、穿戴、玩乐,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
上舟是高干子弟,但他身上完全没有纨绔子弟的习气和优越感。他学习很刻苦,刚来的那个学期,他不仅要努力跟上当时的讲课进度,而且要努力补上落下的功课。为此他课余时间抄写我以前的听课笔记,有八、九门课之多,有问题我再给他讲解答疑。我班的瞿安连与上舟家很近,学习也很好,也常去他家一起帮助他学习。由于福建的中学强调大量做题,高强度训练,而我们四中的教学更注重举一反三,不搞题海战术,所以更需要有学习的自觉性。上舟很聪明也很努力,他很快就适应了四中的教学方式,跟上了教学进度,他少学了一学期的课,居然期末考试成绩很好。后来高中毕业时还以优秀的成绩考入清华无线电系。
上舟为人谦和、开朗、真诚,与同学们关系很好,所以很快就融入了我们班级。当时四中是男校,有一阶段班上一些同学忽然心血来潮,兴起剃光头运动,有的同学很舍不得漂亮的分头,拖了一段时间才犹犹豫豫地剃了,上舟是属于二话不说就剃了光头的,也可见他性格爽快,结果全班都成了“和尚”,一时成为笑谈。上舟很注意向别人学习,有一次我看到我俩共同的好友张泰山清晨踏雪在马路上练长跑,就告诉了上舟,他认为这是锻炼身体和意志的好方法,也开始练起了长跑。他还热心地带动其他同学一起锻炼,瞿安连原来对自己的游泳技术不很自信,正是上舟鼓励他一起去考工体的深水区游泳,使他得到了提高。
当年学校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要热爱劳动,不脱离劳动人民。学校曾经组织我们学习劳模时传祥,背上淘粪桶走街串巷,深入普通居民住宅去淘粪。还组织我们背着行李,长途行军三十多里路,到西北旺农村去劳动锻炼。在这些活动中,上舟都表现得很好,不怕苦不怕累。由于上舟积极要求进步,德智体全面发展,与同学团结互助,得到班级同学和团员们的一致认可,由我做第一介绍人介绍他加入了共青团组织。上舟对别人给他的一点点帮助都会牢牢记在心上,后来在上海工作时期,他向别人介绍我时总是说:“这是我当年的入团介绍人。”
三
1965年秋,我和上舟都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报到时才知道,他分在无001班,我分在无006班,我们都感觉没能同班有点遗憾。当时我们两个班的班主任丁晓青老师和张雨田老师听到我俩互叫外号“船儿”和“大拿”,不禁哈哈大笑,连说:“真有意思!”还学着叫我们的外号。老师的亲切让我们缓解了遗憾的情绪,很快投入到新的学习环境中去。可惜的是我们的大学生活大部分时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很不正常。在这期间有几件与上舟有关的事情却让我记忆深刻,很能体现他的个性。
在1967年1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和上舟在宿舍里议论文革中不理解的事情,忽听外面广播通知让“井冈山捉鬼队”(清华造反派首领蒯大富的骨干队伍)到礼堂前集合,我们也跑去看个究竟。只见有人招呼“捉鬼队”赶紧上大轿车。我本来只想看看就回去,没想到上舟拉着我就上了车。好在车里很黑,有棉帽子半遮着脸,没人认出来。结果才知道他们是冒充“联动”去冲公安部,以便嫁祸“联动”,并寻机破获其组织,我俩也就跟着去公安部门前胡乱比划了一番。事后我才感觉上舟胆子真大,遇事不瞻前顾后。我自己可不敢冒这个险,万一当时被认出来,以我俩干部子弟的身份,肯定会被当作“联动”的暗探而有口难辩,恐怕关押起来吃点皮肉苦是免不了的。他后来在海南工作时敢为天下先,大胆进行超前的改革试验,也与这种性格不无关系吧?
有一次上舟和上南兄弟俩约了我和其他十来个朋友去上方山玩。我是第一次到山里去,对野外生存根本没有概念,只带了一条毯子,一个手电筒,买了几个面包。其他几位也和我差不多,甚至还有两手空空的。可是上舟兄弟俩真是有经验,所带装备齐全,有砍柴刀、绳子、火柴、地图、指南针、锅、米和烤干的馒头片(夏天不易馊)等。尤其是几段截成一尺来长的自行车外胎做火把,在我们进云水洞探险时发挥了大作用,照亮面积大,燃烧时间长,远胜过手电筒。后来爬石经山时口渴难耐,在山上找到一眼小井,他们带的绳子和锅就成了取水工具,否则一群人真要“望井兴叹”了!我至今都没搞清楚他们兄弟俩从哪里学来的这些实用的本事。后来到云居寺,看到上万块石刻佛经,上舟对这些石刻佛经的背景,即南北朝时期出现的“灭佛”事件竟然也能侃侃而谈,我一问才知道他刚读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文革”中我们对学校里的派性斗争不感兴趣,一度成了“逍遥派”,但上舟并没有荒废时光去逍遥,他一直坚持学习耽误的基础课程,也广泛阅读感兴趣的历史、文学等书籍,为后来学业和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上舟在个人的情感生活上对朋友也是非常坦诚的。1969年底我们迁到四川绵阳分校,一天晚上我俩在外面聊天,上舟有些不好意思地跟我说:“我和吴启迪交朋友了,你觉得怎么样?”我对他能把心里的情感秘密告诉我很意外,对他的信任也很感动。我说:“我早都看出来了。”他大为惊讶,问我从哪儿看出来的。我说:“来绵阳之前大家围成一圈玩排球时,你和吴启迪如果接到别人传来的球,总是传给对方,好像心有灵犀似的。”上舟不好意思的笑了,说:“你还挺鬼的!那你觉得她怎么样?”我清楚记得上舟当时那真切的希望得到朋友支持的目光,我说:“我接触不多,感觉她很聪明,也很正直,不娇气。你如果看准了,我一定支持。” 到1970年的春节,学生们都盼望能休息几天,可是工军宣队却规定不准离开建校工地,过所谓“革命化春节”。我和上舟、晓星、萧云四位原四中的老同学对这些“左”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很反感,决定到峨眉山去一趟。出发的那个夜晚,吴启迪来给上舟送行,我注意到她为上舟担心的神情,心里不禁在想:“上舟真有福,还有人牵挂着他。”在那个年代吴启迪的担心确实不是多余的,我们“峨眉四杰”返校后,受到了上纲上线的批判,到3月份毕业分配的时候,我被从留校名单中剔除,分配到黑龙江小兴安岭林区的铁路工程队劳动锻炼,上舟则被分配到云南昆明邮电器材厂。从此两个好朋友一个在东北边疆,一个在西南边陲,相隔万里。
1970年的国庆节后,正在深山沟里的我忽然收到上舟从昆明寄来的信,邮戳上的发出日期记得好像是7月份,辗转好几个月才收到。信中夹着一张他和吴启迪的合影,看他们一脸幸福的表情,又像有点不好意思,我猜这是他们两人第一次合影吧。上舟就是这样,他内心感受到的幸福,总会与老朋友一起分享。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有时会想:我们大学时期最好的青春年华,因为遇到“文革”而失去了许多,可是上舟与吴启迪的相知相爱,却是他大学期间最重要的收获。他俩能力都很强,是我们同学中的佼佼者,一生相互激励、相互支持,在各自的事业领域内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俩都没有官架子,与同学平等相处,帮助过好几位同学解决困难,在同学中口碑很好。我成为他们当年纯真爱情经历的一个见证人,也算难得的荣幸吧。
四
1994年我从吉林大学调到招商局上海金山工业区工作,1997年上舟从海南调到上海市经委,仿佛命运的安排,时隔27年老朋友又相聚在上海。那天我去看望他,吴启迪因担任同济大学校长自然是很忙,无暇作陪,我俩就在同济大学宿舍区的食堂吃中饭,边吃边聊,非常高兴。这可是我俩唯一一次单独在一起吃饭,对我们来说形式上的讲究完全是多余的。上舟让我尽量给他多介绍些上海的风土人情和企业情况,我说我只是在一个基层单位,了解的情况很有限。上舟很诚恳地说,基层的实际情况很重要,解剖麻雀嘛,就是需要多了解实际情况才能做好工作。上舟这样说并不是客套,他在市经委主管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对我先后工作过的外资和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的情况特别感兴趣,见面就问个底儿朝天。
上舟到上海工作后,我俩来往并不频繁,因为我们是那种真正关心对方、替对方着想的朋友。他曾对其他同学说,何吉林很有志气,没找他帮过几次忙,都是凭自己努力。事实上为自己转换工作单位我找过他两次,而为解决企业的关键问题还是请他帮过许多忙。因为我曾亲眼目睹他工作的繁忙和劳累,在公众场合他总是神采奕奕,单独和我在一起时才会显出些许疲态,所以自己能解决的问题我绝不给他添麻烦。1999年8月5日上午,我去经委找他,中饭后屋内只剩我俩时,他显得非常疲劳,不停地抽烟。我劝他好好休息一下,准备告辞,他却坚持再聊一会儿,说就是开了几天夜车准备会议材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不一会儿同济大学校办来电话,告知吴启迪因急病住院,他才匆忙走了。后来得知吴启迪是患了急性坏死性胰腺炎,几次从死亡线上被抢救过来。我去探视时,上舟守候在医院,他忧心忡忡的神情让我体察到他们夫妻之间深厚的感情。上舟的负担更重了,两年后被查出肺癌,年年要化疗,却始终非常乐观顽强,没有停止工作。
上舟有过海外留学和海南创业的经历,眼界开阔、观念开放,对企业很熟悉,因此对我这个“下海”的教书匠帮助很大。2001年当招商局金山工业区被一些领导搞得濒临倒闭时,我对是否要跳槽犹豫不决,上舟对我说:“你早就该跳出来了!”都说响鼓不用重锤敲,可我不是“响鼓”,一时没能领会,上舟又敲了我一下:“你的脑瓜儿还没进入市场经济,董事会都不想做的事情,凭你们几个人努力就能搞起来吗?”我这才恍然大悟,下了跳槽的决心。于是上舟介绍我进入位于松江出口加工区的美资企业华微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工作,他还特别关心地嘱咐我:“我只能帮你介绍,能不能站住脚可要靠你自己了。” 在他的启发下,我意识到不能再按照过去国有单位的老观念老习惯做事情,开始努力地学习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及集成电路行业有关政策,以及出口加工区、海关、商检、工商、税务、基建和供电等多方面知识,加上多年工作积累的协调沟通能力,很快理顺了工厂建设中的各种关系,保证了一座现代化的CMOS图像传感器工厂顺利建成投产,也算没辜负上舟的期望。其间上舟也帮助解决了落实集成电路行业优惠政策和供电等许多难题。
后来因与华微老板在用人理念上的分歧,我决定再次跳槽,上舟是赞同的,他又给我介绍了华虹集团一个新成立的研究所。同时我国集成电路行业著名专家陆德纯也给我介绍了一家温州民营企业的董事长,他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新成立一家从事汽车电子产品研发的公司。两相比较后,我不想在国企中混两年退休,决心到民企中闯一闯。对此上舟没有认为薄了他的面子而不高兴,他深知民营企业发展的不易,还一再嘱咐我:“你们要尽快搞出好的产品来,我就好帮你们说话了。”经过两年多努力,我们科博达公司开发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汽车电子产品,成为国内同类产品中唯一得到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认可、有资格直接给汽车主机厂配套的产品。其后又在德国奥迪新部件的全球招标中,与德国博世等行业巨头同台竞争并胜出,成为第一个实现与国外著名汽车厂商同步开发新车型电子部件的本土企业。
上舟很了解汽车行业突破关键技术和零部件采购权被外国垄断的困难,所以对我公司取得的成绩非常高兴,甚至抱病在家里接待了我公司董事长。那次他刚做完化疗,牙床都肿了,可是却很有兴趣地和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了解我们的情况和需求。在他的帮助下,张江高科技园区解决了我公司建设汽车电子基地急需的土地问题,张江园区对我公司日益重视,成为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上舟这样做,不仅是对老朋友的帮助,更是他对发展中国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一贯抱有的热忱使然。
五
今年四月底我去北京参加清华百年校庆,四中我班的老大哥武晓立约我和上舟参加高中同班聚会,可是上舟却说不能参加了,而且让武晓立转告我:回上海后和他联系。这在上舟是很少有的事,凡同学聚会他都积极参加,甚至直接从机场赴会,没有一点官气。当时我们都没有多想,因为知道他当了中芯国际董事长,非常忙。回上海后不久,四中上海校友会又组织聚会,才听说上舟可能住院了。我赶紧打电话联系,听到他说话很费力,我不禁心里一沉,我让他第二天午后好好休息一下,四点以后再去看他。没想到第二天下午两点半他就打来电话,问我怎么还没去,我感觉到他急迫的心情,马上赶到瑞金医院去了。走进病房,我没想到他会病得变了样,头发掉了很多,人也有些浮肿,插着氧气管,说话很费力,失去了往日的奕奕神采,我心里很难过。可是上舟却很平静,他对我说:“已经开始倒计时了。”我安慰他说:“人的意志对免疫功能的发挥很重要,你一定要有信心。”他说:“我如果不坚强,也就挺不到今天了。”是呵,十年病痛的折磨只有他自己知道,在我们同学面前谁都看不出他是个身患癌症的人。当我问起是否在中芯国际的工作太累才导致病情突然加重时,他却以轻松又欣慰的语气说:“工作不累。总算把前任遗留的问题都解决了,中芯国际又开始盈利了,我也可以把担子交出去了。”我知道中芯国际是他按照新的模式引进的国内第一家特大规模集成电路企业,是行业发展的一个突破性标志,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很重的。因为过一会儿我们大学的同学张文义要来,上舟想动员他接替董事长,我想让上舟好好休息一下,就告辞了,说过些天再来看他。他说:“你下次来,多跟我说说外边的新闻和同学们的情况。”我猜想,这是他意识到来日无多而流露出的生之渴望吧?那一天是5月9日。
半个月后,上舟的老朋友张泰山特意从北京赶来,通过院长批准才和上舟见了一面。泰山对我说,如果有机会就去多看看他吧,恐怕见一面少一面了。5月23日我再次去医院,可是被秘书挡了驾,我只好把一份都江堰日报关于江上舟资助震区残疾学生的文章交给秘书,那是他心中的另一份牵挂。
我始终惦念着上舟的病情,特意选了6月5日星期天去医院,他的亲属带我进了病房,这次要戴口罩,规定探视不超过五分钟。上舟见了我非常高兴,对他的小妹和弟媳说:“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我们才是真正的君子之交淡如水!”那天上舟精神很好,谈兴很浓,可为了他别太累,我就尽量多说让他听着,说到学生时代的趣事,他很开心。他弟媳在旁边说,难得他这样放松和高兴。很快五分钟时间到了,我们相互依依不舍地道别,他又一次平静地微笑着说:“倒计时了,就不方便和你握手了。”我不愿相信倒计时,谁知这次见面却成了好朋友的永别。他留在我心中最后的印象,是坦然的、平静的笑脸。
上舟去世后,我赶到设在康平路办公室的灵堂吊唁。面对他的遗像,从来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我,也不禁“泪飞顿作倾盆雨”了。最后一次去医院看他时,我是带了照相机的,因为我想到相交一世,我俩却没有一张单独的合影。可如果合影我就要摘下口罩,他也可能会伤感,对他的健康不利,我还是把愿望藏在心里了。就这样,两个相交一辈子的老朋友,只能是生者和逝者的遗像在一起合影了。为悼念上舟,我撰写了一幅挽联:“最可赞四十载为强国奋斗献一腔热血重大专项留青史,怎能忘半世纪结挚友情深却惊闻讣音泪洒浦江送君行”,不惮笔拙,聊表心意吧。
在江上舟的告别仪式上,吴邦国、习近平、刘延东、俞正声四位政治局委员送了花圈,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全部出席,这样高的规格代表了国家和上海市对江上舟一生贡献的充分肯定。当我走到吴启迪面前与她握手时,我说:“你失去了最亲密的伴侣,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千万要节哀,多保重!”她含泪告诉我,上舟去世前经常提到我,我也禁不住潸然泪下。愿上舟一路走好,老朋友你太累了,安息吧!
何吉林(65届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