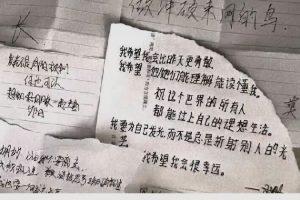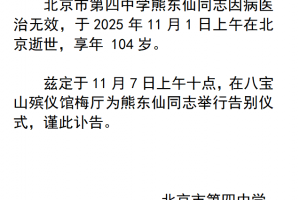郝柏林先生戊戌年初辞世。经校友提醒,我才意识到与郝先生竟有几分渊源,三个关键词:北京四中,复旦大学,理论物理。
在四中读书时,闻听郝先生之名(曾任中科院理论物理所长),当时并不知郝先生也是四中校友。记得还与同学议论“柏林”是读作“Bolin”还是“Bailin”;后来大学讲座介绍郝先生都称“Bolin”,便以为Bolin为正音;却又见Wikipedia上郝先生英文签名和各处论文均做“Bailin”,又糊涂了。复旦物理苏汝铿教授(此公老顽童)当年教我量子力学,苏老师一口独特的北京求学广东乡音的上海话,凡提及郝先生,将“柏”读作“be”,完满解决了读音难题。

物理系师生常把郝先生传得很神,总说他是朗道的关门弟子。苏俄的列夫· 朗道(Lev Landau,196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是一辈传奇,在物理学上有“朗道十诫”之说,堪称前苏联理论物理第一人。朗道和他的学生栗弗席兹合著的 《理论物理教程》是空前而可能“绝后”的巨著。想成为朗道弟子(研究生),必须通过人称“朗道势垒”的一套考试(朗道仅称之为“理论物理最低标准 Theoretical Minimum”)。 从1933到1961近30年,总共只有43人通过考试(名字由朗道亲手记录在笔记本上)。北师大物理赵铮教授在书中透露[1],中国留学生,只有两人曾通过“朗道势垒”。第一人用了二年,朗道没有收他,而是让他直接去教书;另一位就是郝柏林。
朗道⼗诫 (The Ten Commandments of Landau) 指朗道推导出的10个公式,内容为: 1. 密度矩阵 ;2. 电⼦的朗道抗磁;3. 第⼆类相变理论;4. 铁磁畴理论 ;5. 超导中间态 ;6. 原⼦核统计理论;7. 液氦 II 的超流理论;8. 量⼦电动⼒学中物理质量与初始质量的关系;9. 费⽶液体理论;10. 组合宇称守恒原理。
势垒 (Landau barrier) 借⽤物理术语,指的是很⾼的势能,对于能量不够的粒⼦形成壁垒束缚,只有能量极⾼的粒⼦才能通过“势垒”到达新区。
这段传奇郝先生自己讲来最精彩[2]:
1961年10月27日我到达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提出要做朗道的研究生。系秘书查了课表,三天后在大课教室外面,等候朗道课间休息。我对朗道说明来意后,他说:“您知道,我不接收没有通过理论物理最低标准的学生”,(俄语习惯对生疏者称“您”)。我说,知道,我会通过。他又说,“我担心您会落入极其困难的境地”。我说,“那我就尝试从那种境地里闯出来”,用的是俄语中最坚决的表达方式。朗道说,“好吧 ,那您就试试吧 ”,并给了电话号码 ,要我准备好就打电话定考试时间。我又问,可以参加您的讨论班吗?他说,每星期四上午11点,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参加。
我知道有几位中国同学曾经试考过最低标准,但没有人真正通过。于是稍事准备后就打电话到朗道家里。考试定在11月11日上午,在物理问题研究所理论室朗道自己的房间里。他让我坐在办公桌前,拿一张白纸写了个不定积分,就到走廊中去同别人谈话。过一会儿,他进来从后面看了一下,看到已经走上正路,就说,够了,够了,又写了另一个问题。记得有一道题是要简化一个比较复杂的矢量分析表达式。由于我的数学知识基本上源于自学,解题实践不足,于是采取了最有把握的办法,把矢量关系全部用单位对称和反称张量写出来,再按爱因斯坦规则缩并指标。朗道看到以后,大笑了几声,告诉我怎样走捷径。
我事先从苏联同学处听说,同朗道考试,要看谁先说“再见”。如果一道题做不上来,你就得说“再见”,以后还有机会再试一两次。如果朗道主动说“再见”,那是个好征兆。我做了5道题后,朗道拿出三张打字纸,并且说“矢量运算您稍慢一些,不过会习惯的。再见。”那三张纸上印着接受其他各门考试的人名和他们的电话,还开列了研读《教程》准备考试时可以略而不读的章节。
郝先生1959年赴莫斯科,本意在跟随朗道做学问,穿越“朗道势垒”志在必得。可惜造化弄人,朗道1962年初严重车祸,虽在多方救治之下又存活了6年,但天才已逝,再未能回到物理学。因这一番变故,郝先生没能进入朗道弟子名册,实属憾事。郝先生低调,从不说自己是朗道门生;只说当年下功夫研读《理论物理教程》和通过“最低标准”,如何受益终生。
郝先生在学术上诸多建树,远非本文所能介绍[3]。杨振宁先生做过如下评价[4]:
郝柏林教授是中国最富才华和最全面广博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在范围很广的诸多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包括生物学:他开创了研究细菌进化途径的多维方法。事实上他称自己为一名游击队战士,我很以为然。
郝先生自称“游击战士 guerrilla fighter”,不断变换学术坐标和方向;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知识与信息世界的游牧民。随时学习随时迁移,终身学习终身焕新,这是了不起的本事。郝先生自称编了45年程序的老程序员,在大众还没有见过计算机的时候就意识到computation的未来,开始借助数值计算的力量,探索传统解析方法力有未逮的非线性、混沌、复杂系统等领域。北京大学陈平教授曾是耗散结构、复杂系统和混沌领域的鼻祖之一伊利亚· 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学生。据陈老师回忆,混沌研究刚崭露头角时,普里高津尚不以为然。首先转变普里高津观念的正是郝柏林。有一类有趣的化学反应称为B-Z反应,反应液在两种状态(比如不同颜色)之间发生周期性的振荡(在此发现之前通常认为化学反应不可能发生振荡)。普里高津及其合作者针对B-Z反应提出一个数学模型称为“布鲁塞尔振子 Brusselator”,这个模型有混沌行为。郝先生用计算机数值求解,画出了布鲁塞尔振子螺旋状的三维混沌图像,普里高津大为兴奋,十分赞赏。郝先生绘制的一米宽半米高的混沌图,被普里高津挂在办公室墙上,成为一幅科学艺术收藏品。
B-Z反应 (Belousov–Zhabotinsky reaction) 1950年代Belousov在研究三羧酸循环时⾸先发现,反应液在⽆⾊和黄⾊两种状态之间发⽣周期性的振荡,最初使⽤的催化剂是Ce4+/Ce3+,还原剂是柠檬酸。1961年,Zhabotinsky重新研究了这个反应,⽤丙⼆酸代替了柠檬酸,并且对反应机理作了⼀些解释。此后⼀⼤类著名的化学振荡反应都被称为B-Z反应,其中最常见的是铈作催化剂时,丙⼆酸在稀硫酸⽔溶液中被溴酸盐氧化的反应。
布鲁塞尔振子 (Brusselator model) 在理想情形下描述自催化反应(如B-Z反应)动力学演化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方程中有二种物质X和Y,二者既是反应物又是生成物,Brusselator 微分方程组表达的是:X和Y浓度的时间变化率由二者浓度非线性的耦合函数决定。

牛津大学有个教席称为 Professor for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翻译成“科普教授”无伤大雅。窃以为郝先生也当得这个头衔,在“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方面与专业领域有同等的功力。我虽只在讲座场合见过郝先生二三次,读文字作品限于二本小册子[5],然而其言其文透彻犀利,率真不讳,每次接触都印象深刻。以郝先生的“多才多艺versatile”,朗道一般的傲骨和批判精神,长期研究复杂系统所积累的思考,讲起科普经常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郝先生有一系列“从若干自然规律看某些社会现象”的讲座,我听过一个很早期版本。那回郝先生不怕得罪人,讲座标题赫然包括给“文科生”的建议,不少观点值得思考。开宗明义,郝先生强调他所讲的是从自然科学出发的“类比和联想”,类比是不完备的,联想也只限于事物的表象层;两者都不能代替对社会现象的符合科学方法的调查和研究。讲座中郝先生说了不少“大实话”,比如:
1
人文学者写文章要有引文,写书要有索引(看来当时这还没成为实践上的普遍事实);不客气地说有些文章分不清哪些是他人观点,哪些是作者独创。
2
下论断(尤其是历史论断)之前建议做数量级估计。社会作为复杂系统参数极多,“心中有数”才可能辨别主要因素,以免闹笑话。郝先生当场对有史以来人类所说过的语言单词总数做了一番估计,还特意引用了数学分析中的确界原理(任何实数集合如果有上界必有上确界)。
3
诸子百家虽美,不建议初学者沉浸其中将其神话,以所谓中国文化的“整体”和“综合”傲视西方科学的分析传统,须知无分析何来综合!郝先生认为周易阴阳充其量只是 “人类幼年时期的天才创造” ,先秦哲学更像是“人类童年的故事与幻想”,在以科学方法建立的知识体系下思考,更建议“薄古厚今”。
4
以“相变临界点”类比社会和人生的突变。什么情况下平时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会起决定作用?临界点/突变点附近。比如高考分数线,一分之差可能导致个体天差地别的生活道路。然而,这一分的“涨落”只对考分恰好落在分数线(临界点)附近的人才举足轻重,这时小涨落可能被剧烈放大。高分考生不必担心,低分考生担心没用;只有考分在临界点上下的人才会十分焦虑。这时一些次要的因素(另一些“小量”),例如家里有没有钱交“赞助费”,爹娘有无“人脉后门”,都会影响最终命运。由此郝先生发明了一个“关于革命者的泰勒级数展开理论”:零阶近似下,革命者和群众都一样(都是人);一阶近似下,革命者都差不多,都有革命理想走革命道路;只有在临界点critical point,一阶项为零,高阶小量才起作用(学过微积分的读者都懂),关键时刻方见真英雄还是假革命。
泰勒级数展开 (Taylor series expansion) 一个解析性质足够好的函数可以围绕一点级数展开;在物理学中,经常将一个复杂函数对某小量“逐阶”级数展开为零阶项+一阶项+二阶项+…的形式,通常前边是“主导项”,后边往往是可忽略的是“高阶小量”。
5
一个复杂系统的状态须要极多(甚至无穷多)变量来描述。粗略地讲,不妨把这些随时间演化的变量分成两大类:慢变量和快变量。一个人群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字是慢变量,而具体个人的生老病死是快变量;快变量总是受慢变量制约甚至控制。郝先生将人生类比成一个巨大的动力学微分方程,方程中既有代表个体的变量也有代表社会的变量,每个人都关心个体变量随时间的演化。个体变量是快变量,社会变量是慢变量。在“人生动力学微分方程”中,最低阶近似下,社会历史变量可以被当作常数,于是它们完全决定了个人变量,决定了人生轨迹。个体不能选择自己诞生的时代与环境,只能在这个“近似常数”的背景下,被环境塑造。一个伟大人物可以“改朝换代”,但不能创造出一个完全与过去无关的新世界。认识到对社会发展起着控制作用的慢变量,对于作为快变量的人生可以具有极其积极的作用。

最后我想再回到物理学,毕竟这是我与郝先生最大的渊源。19世纪后半叶物理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当时metaphysics已被译为“形而上学”,于是把physics称为“形而下学”。“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以为物理学(所有科学和数学)不只是“器”。郝先生曾写道“物理学是讲道理的学问”,“物理教育是文化教育艺术教育”,“物理学是一门历史科学[6]”。如果文化、艺术、历史是“道”,那么物理学(数学和科学)既是Tao of mind思想之道,又是Tao of nature自然之道。请允许我略作改动地引用郝柏林先生:一部物理教材目录,就是一份物理学史提纲。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在物理学发展演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物理学的发展不断挑战和克服人们的保守与偏见。然而历史的很多时候,社会和文化的慢变量使人气馁。这种时候也许需要等待,正如马克斯· 普朗克所说[7]: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并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们信服并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因为这些反对者们最终总会死去,而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数学和科学教学的愿景之一就是把更接近真理的认知传授给成长中的新一代人。
[1] 赵峥,《探求上帝的秘密—从哥白尼到爱因斯坦》,北京师范⼤学出版社,1997
[2] 郝柏林,朗道百年,《物理》 37, 2008
[3] 领域覆盖理论物理、⾮线性科学和理论⽣命科学。成果覆盖固体电⼦能谱和声⼦谱、⾦属红外性质、⾼分⼦半导体理论、统计物理、天线理论、地震分析、混沌动⼒学、符号动⼒学、理论⽣命科学、⽣物信息学和计算⽣物学等。
[4] Chen-Ning Yang, C N Yang on Hao Bailin, Peregrinations from Physics to Phylogeny, World Scientific, 2015
[5]《相变和临界现象》,《漫谈物理学和计算机》,二本小册子。通俗而不浅显,曾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6] 郝柏林,物理是一种文化,《物理通报》 12,2012
[7] Max Planck: A new scientific truth does not triumph by convincing its opponents and making them see the light, but rather because its opponents eventually die, and a new generation grows up that is familiar with it.